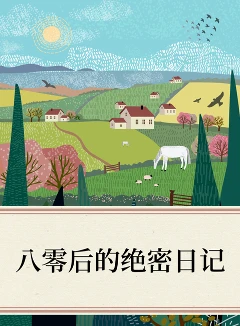第26章 白鶴涉水(二)
螢螢似乎在聞他的氣味。
程瓔呆呆地看著,他想起自己身上有粘膩的汗跡,慌張地掩住她唇鼻,“螢螢,你離遠些,我身上有難聞的味道。”
難聞嗎?分明很香甜。
漆螢把那只阻止她的手壓在一側,病弱的他像一只引頸待戮的傷鶴,分不出多余氣力掙扎,只能被壓著,看著她如小犬一般貼過來,嗅聞著自己。
程瓔聞見衣上混濁著藥氣的淡酸,難堪得想要逃離,甚至不敢再去看漆螢的神情。
壓在他上空的那道影子離去了,他才顫巍巍睜開眼睛,惶恐不安地問道:“螢螢,你方才在聞什麼?難道阿兄身上有什麼東西嗎?”
漆螢沒心思理會他,她饜足,打算離開這里。
程瓔慌張地爬起來,“螢螢你別走,阿兄身子不舒服,你留下來陪我好嗎?只留一會就好了,螢螢別走……”
他從床榻上摔下來,衣襟都松散了,白玉似的肌膚裸露出來,烏發堆疊在纖瘦的腰間,抬頭看著她,眸中水色瀲灩。
螢螢,別走。
漆螢聽見了身後動靜,但她不能再回去。
她記得方才那女郎的話,再吸下去,他就要死了。
“螢螢……”
程瓔渾渾噩噩地蜷縮在地上,漸漸分不清現實與夢境,怨恨這副虛弱不堪的身子,怨恨他離了螢螢就變得酸澀的五髒六腑。
也怨螢螢,為什麼要走,為什麼一定要丟下他……
恍惚又入了夢,周遭冰天雪地,冷得骨骼發顫,有個瘋子在給他灌苦鴆酒,他說,你妹妹死了,你為人兄長,怎麼不下去陪她?
他想說螢螢沒死,她很好,你想搶走我妹妹,你想把我們分開……
苦藥淹了喉嚨,想吐,吐不出。
那人又挖了個黑漆漆不見底的洞,說要埋葬了他。
他惶惶哭鬧著:“螢螢,有人要害我……”
漆螢出了門,那個金色眼瞳的小東西端坐在窗台上,似乎是在等著她出來。
蹭了蹭她伸來的手指,跳下窗台引路。
回到廂房,那女郎盯她看了半晌,疑神疑鬼道:“沒把人吸死吧?”
漆螢不答,她又看向烏圓,小貓搖頭。
枕微好奇道:“你吸的是誰的陽氣?”
漆螢不知那人是誰,冷淡道:“小鶴。”
“小賀是誰?府中的侍從嗎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不認識的人啊,那你覺得現在如何了?能想起來什麼嗎?”
漆螢思索道:“有魚在啃我的皮肉。”
“那應該是若無河里的事。”
枕微嘀嘀咕咕道:“看來還是不夠,去了這麼久,怎麼只吸食了這麼一點?你是不是不會?”
她愈發覺得可疑,“你是怎麼吸的?”
漆螢提起小貓後頸,去嗅探她血肉的氣息,隨後放下,淡淡朝馮女郎睨了一眼。
枕微瞬間緘默,無話可說。
“哎、呀!不是干吸,虧得你還做了十幾年道士呢,你們道家的陰陽采補之術你不知道嗎?采補、采補他啊!”
“什麼是采補?”
“活人的血肉之軀好比器皿,需要有孔隙,才能把里面的水傾倒出來,而男女陰陽交合、神迷魂亂,便如同打開了小孔,這個時候,是最適合我們攫奪陽氣的。”
“男女燕好你該懂的,你先探查一番,若那人的皮囊、陽物皆是上乘,你用一用也無妨,若人丑物短,就讓他自瀆,或者用其他物件褻玩到他精竅失守,恍惚無神,再進行采補就好了。”
枕微又問:“小賀的臉長得如何?”
“很白。”
“一白遮百丑,胯下陽物大嗎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最好要白淨均勻的,否則灰鼠一般,看著惡心,總之,按照你的喜好來挑,安定公府里沒有,我們也可以去外面找,千萬不要像那些葷素不忌的老色鬼一樣,品味太差了些。”
“對了,你聞小賀的時候,他是什麼反應?”
“在哭。”
“嚇哭了嗎?這麼嬌氣,也無妨,等你采補的時候他舒爽了,自然就不哭了,說不定還會纏著你,小郎君都是這樣的,麥芽糖一樣,黏黏糊糊。”
“天快亮了,你晚上再去找他吧,你要記得現在的身份是安定公府的女郎,在小仆房里白日宣淫被捉到,程瓔一定會被你氣死的。”
“程瓔?”
“就是你那個便宜兄長,等過幾日你想起來了,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。”
天色漸明,有叩門聲。
尤青在外面大吐苦水:“女郎,郎君真是糊塗了,我給他喂藥,他非說我在給他灌毒酒,還要活埋了他,現在鬧著要你去救呢,女郎你過來看看吧!”
枕微提醒漆螢:“他說的這人就是程瓔,你跟去看看。”
漆螢開門,尤青一張苦瓜臉,“熱症退了,也許是夢魘呢,女郎去哄哄吧。”
纖瘦的鶴蜷縮著,仿佛躲在巢中。
漣漣清淚洇濕了枕衾,他猶在夢魘,一聲一聲念著“螢螢、別走、救我……”
漆螢想起枕微方才所言,目光探入他腹下。
若白淨均勻,便可自用。
他散開的衣襟下,膚如瓊雪,漆螢的手指從他喉結往下探去,到腰腹間,有細微起伏,少時修習君子六藝,腰身纖穠合度,有少年氣。
錦衾被掀開,腰腹下只穿了一件輕綢里褲,胯間藏有鯉腹般鼓脹的曲度,肌膚上仿佛有輕羽在撓,他難受,往後退縮。
手指探入褲腰,往下撫去。
冰冷的指尖激起他一聲嗚咽和扭動。
她毫不憐惜地握住,那“鯉腹”在幾息之間便腫脹異常,盈斥她掌心,如木杵般硬挺粗長,把綢紗高高地頂起,隱約可見其令人側目的形狀。
“嗯……”
未經人事的處子不受控制地呻吟一聲,難受地咬著唇肉,偏過頭去。
有星星點點的前精滲出來,洇濕了綢紗,薄而清透,鈴口的顏色和形狀清晰地顯出來,緋紅一片,如牛乳澆在海棠上,甚至隱約可見中間下陷的,楚楚翕動的小隙。
她隨意動了動手指,又有精水如細泉上涌,甚至順著陽物本身流淌到她手上,滑膩潮濕,仿佛是池水中一尾真正的紅鯉。
如何褻弄,漆螢不太懂。
那陽物隨著他的身子顫顫亂動,她用手指圈住,握緊,就著精液的濕潤,緩慢移動。
郎君口中難以抑止地,溢出些哭聲,身子純淨得連自瀆都少有,怎能受得了她纖涼的指。
那麼敏感,只消輕輕一動,便在她掌中脹大三分,肥紅穠艷的鈴口,隔著一層乳白的綢,顫巍巍可憐。
被灌鴆酒的噩夢幾度變幻,夢境中,程瓔仿佛置身於天上宮闕,有神女用法術蒙著他的眼,像是逗樂似的,去褻玩他的下體。
那纖涼的指隨意地輕捋了數下,便撤走了,他脹痛得好難受,想哭泣,卻不知為何而哭。
無法疏解的難受,或者是,他的貞潔,被褻瀆了的處子身。
他只是尋常凡人,可為何偏要受這般折辱?
不知後來被丟棄在哪里,他赤裸著,腫脹的下體暴露在冰冷的空氣中,沒有遮掩,說不定還會有仙人從此地路過,看見了,笑他淫蕩不堪。
又哭了,清淚涔涔。
這般害怕麼?漆螢感覺有些無趣。
她伸手拭淚,才發現手上沾了些牛乳一樣的東西,不是透明的水液。